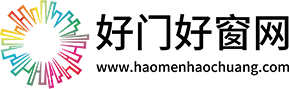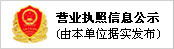北京時間12月27日消息,據國外媒體報道,在《星球大戰:最后的絕地武士》(Star Wars: The Last Jedi)上映之時,許多人在銀幕上都見到了女主角蕾伊向年老而又孤獨的盧克·天行者學習如何掌握原力的場景。在觀影的同時,有人也提出了一些顯而易見而又歷久彌新的問題:科學上,特別是量子力學中是否有類似原力的東西存在?物體能否在遠距離上被突然操控?
答案,或許就在現代物理學中。
在最初的《星球大戰》電影中,歐比旺·克諾比對盧克·天行者說,原力“環繞在我們周圍,滲透我們;有著凝聚整個星系的能量”。
現代物理學家已經知道,宇宙中存在4種基本力(又稱基本相互作用):強核力、弱核力、電磁力和重力。從最微小的原子,到龐大的行星,這4種基本力都在連接宇宙物質中扮演著重要角色。
不過,它們可能都不我們所要尋找的“原力”。歐比旺·克諾比、尤達大師和盧克·天行者,他們都可以用精神來進行遠距離的心靈感應并移動物體。
這些有可能嗎?如何用物理學定律來評價這一切?
對于交流的速度能有多快,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給出了限制,而終極的速度限制就是光速。因此,如果你想把帝國進攻的消息傳遞給奧德蘭的居民,那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延遲,因為即使是信息以光速傳播,也還是需要時間的。
那么,對于遠距離的信息傳遞,量子力學又會怎么說呢?我們還是不能突破愛因斯坦的光速限制,就算有千年隼號也不行。在電影中,韓·索羅說千年隼號可以在12秒差距(parsec)內完成一次科舍爾星球走私航程,然而秒差距是一個距離單位(1秒差距相當于3.26光年),而不是時間單位。
 ink="" style="border: 0px none; vertical-align: middle; display: block; margin: 0px auto; max-width: 640px;" />黛西·雷德利在《星球大戰:最后的絕地武士》中扮演女主角蕾伊
ink="" style="border: 0px none; vertical-align: middle; display: block; margin: 0px auto; max-width: 640px;" />黛西·雷德利在《星球大戰:最后的絕地武士》中扮演女主角蕾伊不過,通過一個量子力學把戲,你可以用一種特殊的方式把兩個粒子聯系起來。先把它們分開,然后觀察其中一個粒子對另一個粒子的效應。盡管兩個粒子相隔很遠,但當對其中一個粒子測量時,另一個粒子似乎知道測量動作的發生和結果。這種現象被稱為量子糾纏(quantum entanglement),其詭異性要遠勝于《星球大戰》創作者喬治·盧卡斯的任何想法。
量子糾纏可以在實驗室里用光子進行演示。當兩個光子被分開很長距離時,它們之間依然存在聯系。如果你測量其中一個光子,另一個光子的狀態也會發生改變,無論二者距離有多遠。
愛因斯坦并不喜歡這一概念,他稱之為“鬼魅般的超距作用”。然而,現代物理學實驗已經證明了量子糾纏的真實存在。
事實上,喬治·盧卡斯在撰寫《星球大戰》的最初劇本時也受到了量子理論的影響。20世紀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初,新紀元運動(New Age)的思想家提出量子糾纏就是一種將我們都聯系在一起的“力量”。
在物理學實驗中為人熟知的一點是,觀察者可能會與他們測量的物體發生“糾纏”,從而改變測量結果。這在某種程度上引出了我們都“糾纏”在一起的概念。
然而,這只是一個巧合。對于日常物體而言,量子糾纏的影響極為微弱。如果凱洛·倫是一個物理學家,他或許可以操縱幾個光子,使其量子糾纏,但若是想把激光束截停下來,就要困難得多了。
不過,在凝聚態物理學——研究物質凝聚相的物理性質——領域中,“糾纏”現象要更加普遍。固體物理學家研究的是數以十億計粒子的糾纏,他們往往能獲得一些非常新穎的結果,比如在超導領域的發現。一些新的現象,比如超導體懸浮在磁石上方的邁斯納效應,就是宏觀上電子的量子糾纏,或者說是一種鬼魅般的超距作用“力”。而正是量子糾纏的“力”,也催生了所謂的新型“量子材料”。
從某種程度上,原力背后還是有一些真實的物理學基礎。量子糾纏在現代物理學中扮演著重要角色,也是物質和能量之間建立聯系的方式之一。然而,我們很難在大尺度上達到量子糾纏,在活生物中進行觀察就更困難了。
那么,原力能否被視為“一種所有生命體都能產生的能量場”?物理學家才剛剛開始對生物學中的量子糾纏展開研究,并開辟了一個相對較新的領域——量子生物學。只有一些偶然的證據顯示,較大的生物分子可能會受到量子糾纏效應的影響。
量子糾纏在生命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概率似乎很低,但或許正如韓·索羅所說:“永遠不要跟我說幾率!”